武漢長江大橋
| 武漢長江大橋 | |
|---|---|
 | |
| 座標 | 30°32′56″N 114°17′17″E / 30.549°N 114.288°E |
| 承載 |
武漢內環線 |
| 跨越 | 長江 |
| 地點 |
|
| 維護單位 | 公路橋面:武漢市建設局 鐵路橋及橋身主體:武漢鐵路局武漢橋工段 |
| 設計參數 | |
| 橋型 | 鋼桁梁橋 |
| 全長 | 總長1670米 正橋1156米 |
| 寬度 | 公路橋22.5米 鐵路橋14.5米 |
| 最大跨度 | 128米 |
| 跨數 | 9個 |
| 橋墩數 | 8個 |
| 負載限制 | 鐵路橋:中-24級 公路橋:汽-13級 |
| 橋下淨空 | 18米 |
| 歷史 | |
| 建築師 | 武漢大橋工程局 |
| 設計師 | 鐵道部勘測設計院 |
| 施工單位 | 鐵路部大橋工程局、鐵道兵 |
| 開工日 | 1955年9月1日 |
| 完工日 | 1957年9月25日 |
| 開通日 | 1957年10月15日 |
| 統計 | |
| 日交通量 | 汽車近10萬輛、列車約300列 |
| 通行費 | 無 |
| 地圖 | |
| 武漢長江大橋 | |
|---|---|
|
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公布 | |
| 所在 | 湖北省武漢市 |
| 分類 | 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築 |
| 時代 | 1957年 |
| 編號 | 7-1814-5-207 |
| 登錄 | 2013年3月 |
武漢長江大橋位於中國湖北省武漢市,橫臥於漢陽龜山和武昌蛇山之間的長江江面之上,是長江上第一座鐵路、公路兩用橋,因此又被稱為「萬里長江第一橋」。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規劃始於1910年代,由1913年至1948年間曾先後四次進行長江大橋的勘測、選址和設計,但幾次規劃都因經濟、戰亂原因而擱置。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武漢長江大橋的建設被列入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的蘇聯援華156項工程之一,於1950年起正式開始進行大橋的測量和設計,1955年9月動工建造。由於採用了新的管柱鑽孔法取代傳統的氣壓沉箱法,大大加快了大橋的建造速度,使武漢長江大橋竣工日期提前2年,1957年10月正式通車。

武漢長江大橋為雙層鋼桁梁橋,上層為雙向四車道的公路橋,兩側設有人行道;下層為京廣鐵路複線。大橋自建成以來,一直都是武漢市的標誌性建築,同時也是最著名的旅遊景點之一。[1]
早期規劃
背景
武漢三鎮位居中國腹地、長江中游,漢水由此匯入長江,擁有重要的地理位置優勢,曾被孫中山譽為「內聯九省、外通海洋」的大商埠[2]。至清末時期,武昌為湖北省會,漢口為商埠,漢陽也發展了一定的工業基礎。1906年,京漢鐵路全線通車,而粵漢鐵路也在修建當中,建橋跨越長江、漢水連接京漢、粵漢兩路的構思即為各方所注意[3]。據歷史檔案顯示,在武漢建第一座長江大橋的設想最早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提出,用以溝通南北鐵路[4]。1912年5月,中國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被北洋政府聘為粵漢鐵路會辦[5]。詹天佑在進行粵漢鐵路復勘定線的過程中,考慮到將來粵漢鐵路與京漢鐵路會跨江接軌,為此在規劃武昌火車站(通湘門車站)時也預留與京漢鐵路接軌出岔的位置[6]。
第一次規劃


1913年,在詹天佑的支持下,國立北京大學(今北京大學)工科德國籍教授喬治·米勒帶領夏昌熾、李文驥等13名土木門學生,到武漢來對長江大橋橋址進行初步勘測和設計大橋的實習[7],並由時任北京大學校長嚴復將建橋意向代陳於交通部。這一次成為武漢長江大橋的首次實際規劃,當時提出建議將漢陽龜山和武昌蛇山之間江面最狹隘處作為大橋橋址,經武昌漢陽門、賓陽門連接粵漢鐵路,並設計出公路鐵路兩用橋的樣式[8]。當時構思的橋梁結構仿照當時世界著名的最大鋼橋——英國蘇格蘭愛丁堡的福斯橋[9],橋面鋪設鐵路、公路、電車路、人行道。此次規劃雖然未獲實行,但其選址被歷史證明為十分適宜,與此後幾次規劃選址基本相同[3]。
第二次規劃
1919年2月,孫中山寫就了《實業計劃》,闡述了開發中國實業的途徑、原則和計劃,提出中國經濟建設的宏偉藍圖,在其論述中即提到關於武漢修建長江大橋或隧道的選址問題[10]。為連通武漢三鎮,孫中山當時提出「在京漢鐵路線於長江邊第一轉彎處,應穿一隧道過江底,以聯絡兩岸。更於漢水口以橋或隧道,聯絡武昌、漢口、漢陽三城為一市。至將來城市用地發展擴大,則更有數點可以建橋或穿隧道」[11]。1923年,由辛亥革命時的參謀長孫武組織,依據孫中山的規劃思想,編制了《漢口市政建築計劃書》。《計劃書》明確提出,「以漢陽之大別山麓(龜山),武昌之黃鵠山麓(蛇山)為基,架設武漢大鐵橋,可收平漢、粵漢、川漢三大鐵路,連貫一氣之完美」[11]。
由於當時的平漢鐵路黃河大橋在建設過程中為求節省經費、提早通車,因此建築質量較差,僅作為臨時橋梁使用[12]。1921年,北洋政府擬建黃河大橋新橋並施行公開招標,交通部又聘請美國橋梁專家約翰·華德爾為顧問,除籌建黃河大橋新橋外,並請其設計武漢長江大橋[3]。華德爾選擇的橋址與1912年北京大學所擬位置大致相同;設計方面採用簡單桁梁、錨臂梁、懸臂梁混合布置,並主張使用合金鋼建橋以減輕重量,預算建築費用為970萬銀元,華德爾並建議向美商貸款。華德爾的方案曾引起政府關注,擬定橋址也做過實地鑽探,惟由於建設費用龐大,計劃也不了了之。[13]
1927年1月,廣州國民政府遷都武漢;同年4月合併武漢三鎮,設武漢市。1929年4月,國民政府成立武漢特別市政府,進一步推動了武漢的市政建設[14]。同年劉文島任武漢特別市市長後,再次邀請華德爾來華,研商長江建橋之事[15]。華德爾對1921年的設計方案作出了修訂,為保證長江輪船的通行,大橋採用簡單桁梁並設升降梁,全長4010英尺,共15孔,橋面一層由公路鐵路共用,橋面升起時可高出最高水面150英尺。這次計劃同樣由於耗資巨大而無下文,且國民政府正忙於應付內部軍事派系鬥爭,包括蔣桂戰爭、中原大戰等內戰,無暇顧及長江大橋的建設。[16]
第三次規劃
1935年,鑑於粵漢鐵路即將全線建成通車,平漢、粵漢兩路有必要在武漢連通。當時鐵道部曾考慮仿照1933年建成的南京鐵路輪渡,但由於武漢的長江水位漲落幅度比南京大一倍,兩岸引橋工程較困難,被迫擱置鐵路輪渡的方案。同年,由茅以升擔任處長的錢塘江大橋工程處又對武漢長江大橋橋址作測量鑽探,並請蘇聯駐華莫利納德森工程顧問團合作擬定又一建橋計劃。計劃為一座固定式的鐵路公路聯合橋,橋址位於武昌黃鶴樓到漢陽蓮花湖北劉家碼頭之間,全長1932米,設兩台7墩8孔,6、7號橋墩間為大型輪船通航航道,主跨237.74米,以拱形鋼梁架設於6、7號墩之上,橋下在最高洪水位時淨高30米;橋面一層,公路鐵路並列。包括漢水鐵路橋和引橋在內,工程需要花費法幣1060萬元。為了募集資金,還曾擬定了過橋收費、分期還本付息的辦法。惟由於集資困難,結果也不了了之。1937年3月,長江南岸的粵漢鐵路徐家棚站(今武昌北站)與北岸平漢鐵路劉家廟站(今江岸站)之間的鐵路輪渡通航,火車乘渡輪過江從此成為「江城一景」[17][18]。
第四次規劃
中國抗日戰爭結束後,百廢待興,而興建武漢長江大橋的計劃也再度舊事重提。湖北省政府於1946年8月25日舉行會議,決定邀請粵漢區、平漢區鐵路管理局及中國橋梁公司共同組織成立武漢大橋籌建委員會,省政府主席萬耀煌為主任委員,茅以升為總工程師[19];同年9月初中華民國行政院工程計劃團團長侯家源偕同美國橋梁專家鮑曼等考察武漢長江大橋橋址[20]。同年,由中華民國內政部營建司司長哈雄文陪同美國市政專家戈登來漢視察,並有平漢區鐵路管理局局長夏光宇參加[15],當時提出的建橋意見是:鐵路和公路合併可降低造價,位置仍以龜山、蛇山之間為宜;為減少墩數、便利船運,決定改用較長跨度的懸臂拱橋,設4墩5孔,同時考慮到鐵路幹線運輸日益繁忙,大橋可適當提高載重等級。後因國共內戰、經濟困難,國民政府無暇顧及長江大橋的建設,武漢長江大橋的計劃再次擱置。[21]
興建
規劃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不久,時年63歲、自1913年起多次參與武漢長江大橋規劃、勘探的李文驥,聯合茅以升等一些科學家、工程師向中央人民政府上報《籌建武漢紀念橋建議書》[22],提議建設武漢長江大橋,作為「新民主主義革命成功的紀念建築」,並詳述前四次規劃經過和受挫的原因,論述當時中國能建成大橋的可能性與具體工程內容、經費預算(600億舊人民幣)等[23]。中央政府對此甚為重視,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平召開,會議上通過建造長江大橋的議案,並於1949年末電邀李文驥、茅以升等橋梁專家赴京,共商建橋之事[24]。
| “ | 武漢三鎮居國之心臟,為交通之總樞紐,然因長江天塹,南北受阻,此際欣逢中央人民政府已成立,同人等不揣菲薄,建議籌建過江大橋…… | ” |
| ——李文驥(1949年)
,《籌建武漢紀念橋建議書》 |
||
根據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的指示,中央人民政府鐵道部立即著手籌劃修建武漢長江大橋。1950年1月,鐵道部成立鐵道橋梁委員會,同年3月成立武漢長江大橋測量鑽探隊和設計組,由中國橋梁專家茅以升任專家組組長,開始進行初步勘探調查[25]。李文驥當時已抱病在身,仍第五次赴武漢參與長江大橋設計和測量勘探,並堅持工作至1951年6月,同年8月病逝[26]。
專家組先後共作了八個橋址線方案,並逐一進行了縝密研究,所有的方案有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利用長江兩岸的山丘以縮短引橋和路堤的長度[27]。1950年9月至1953年3月,曾三次召開武漢長江大橋會議,就有關橋梁規模、橋式、材質、施工方法等進行討論。1953年2月18日,毛澤東在武漢聽取中共中央中南局領導關於大橋勘測設計的匯報,並登上武昌黃鶴樓視察了大橋橋址[28]。大橋選址方案經中央財經委員會批准確定後,鐵道部立即組織力量進行初步設計[29]。
1953年4月1日,周恩來批准成立武漢大橋工程局(今中鐵大橋局集團的前身),負責武漢長江大橋的設計與施工,彭敏任局長兼黨委第一副書記,楊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長,汪菊潛任總工程師[30]。同年7月至9月,鐵道部派出代表團攜帶武漢長江大橋全部設計圖紙資料赴蘇聯首都莫斯科,請求蘇方協助進行技術鑑定,蘇方為此派出由25名橋梁專家組成鑑定委員會進行研究,鑑定會的改進建議包括稍微調整漢陽岸的橋址、同意採用氣壓沉箱法施工等,且鑑於桁架梁結構的丹東鴨綠江大橋在韓戰中被炸毀時梁部墜落,故處於戰備考慮建議長江大橋橋梁形式改為三孔一聯等跨連續粱[31]。1954年1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務院第203次會議聽取了時任鐵道部部長滕代遠關於籌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情況報告,並通過了《關於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決議》,決定採納蘇聯的鑑定意見、批准長江大橋的初步設計,正式任命彭敏為武漢大橋工程局局長,楊在田、崔文炳任副局長,同時批准了1958年底鐵路通車和1959年8月底公路通車的竣工期限[32]。

1954年,國務院批准了鐵道部聘請蘇聯專家組來華支援的請求。1954年7月,蘇聯政府派遣了以康斯坦丁·謝爾蓋耶維奇·西林(Константин Сергеевич Силин)為首的專家工作組一行28人來華進行技術援助。西林是蘇聯著名橋梁專家,曾於1948年至1949年間兩次赴中國,協助修復東北地區鐵路和松花江大橋,並參加過成渝、天蘭、蘭新鐵路的橋梁建設[33]。西林來到中國後,表示認為長江大橋不宜採用氣壓沉箱法施工,原因是長江水深流急,沉箱需要下沉深達30米至40米,在接近四個大氣壓的環境下,每名工人只能每天工作約半小時,實際作業時間僅有十幾分鐘,而且只能在枯水季節的幾個月內進行施工,必然大大延長施工時間、危害工人的健康,而且需要購置大量特殊設備,加大工程投資。西林建議用管柱鑽孔法,不但能在水面施工,不受深水期的限制,而且不影響工人身體健康,但這種方法當時仍然是一種新技術,蘇聯也尚未實踐過[34]。大橋建設部門對管柱鑽孔法的設計方案經過三個月的討論和半年的試驗,證明確實可行,經請示鐵道部長滕代遠、總理周恩來後,國務院於1955年上半年批准對新方案「繼續進行試驗,並將新舊方案進行比較,也既是黨中央提倡的『依靠群眾,一切通過試驗』的方法」[32]。
1954年2月,在1950年初步勘測的基礎上,由地質部、水利部、鐵道部聯合組成的武漢長江大橋地質勘探隊,開始進行武漢長江河槽及兩岸的地質評估。同年夏秋,武漢遭遇了自1865年有水文記錄以來的最大洪水,勘探隊最終在1955年1月10日完成了武昌黃鶴樓和漢陽龜山之間的地質評價[35]。1955年1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橋址選線技術會議在漢口召開,正式決定選擇龜山、蛇山一線[29]。1955年2月,鐵道部成立了武漢長江大橋技術顧問委員會,作為大橋工程的技術諮詢機構,由茅以升為主任委員,其他委員包括羅英、陶述曾、李國豪、張維、梁思成、劉恢先等。1955年5月下旬至6月初,鐵道部按管柱鑽孔法編制出武漢長江大橋技術設計方案,併集中全國著名的橋梁專家和橋梁建築工程師,舉行了武漢長江大橋技術設計審查會議,對大橋的技術設計、施工進度和總預算進行了周密的審查[36]。同年7月18日,國務院批准了這些報告,標誌著武漢長江大橋建設工程開始進入實施階段[29]。
建設



經國務院批准後,武漢長江大橋於1955年9月1日提前正式動工。武漢長江大橋全部工程除了大橋本身以外,還包括大量配套工程,包括漢水鐵路橋、大橋聯絡線、由丹水池站經江岸西站至漢水鐵路橋頭的漢口迂迴線(今京廣鐵路正線)、江岸站至江岸西站的聯絡線、江岸西編組站、漢西站、漢陽站等設施[37],其中漢水鐵路橋和長江大橋正橋和引橋工程由鐵道部武漢大橋局負責施工,其餘鐵路及跨線橋工程由鐵道兵施工[38]。鐵路從粵漢鐵路武昌南站(今武昌站)起,以立體交叉跨越武珞路、中山路、武昌路、解放路,沿蛇山至黃鶴樓處,橫跨長江,過江後沿龜山以立體交叉跨越漢陽月湖正街,至阮家台處過漢水,又跨越張公堤及仁壽街至玉帶門站與京漢鐵路接軌。早在進行大橋設計規劃的同時,作為武漢長江大橋配套工程之一的漢水鐵路橋於1953年11月27日率先動工興建,兩岸鐵路聯絡線工程也同時開始進行,並於1954年11月12日建成,1955年1月1日正式通車。而漢水公路橋也於1954年10月30日開工興建,1955年12月建成通車,並被命名為「江漢橋」。[39]
蘇聯政府獲悉武漢長江大橋採用管柱鑽孔法施工後,於1955年底派出以運輸工程部部長科熱夫尼科夫為首的代表團來華,參觀長江大橋的施工。最終,西林的管柱鑽孔法獲得了蘇聯政府的認可,同月中國鐵道部與蘇聯運輸工程部簽訂了協議,對這種施工技術作出了正面評價。大型管柱鑽孔法使大橋施工速度大為提高,橋墩基礎工程從全面開工到基本完成僅用了一年零一個多月的時間。1956年10月,大橋各橋墩下沉管柱和從管柱內向江底岩盤鑽孔的工作全部完成[40]。1957年3月16日,大橋橋墩工程全部竣工。長江大橋採用3聯9孔的等跨間支梁進行安裝,使用平衡懸臂拼裝架設法,從武昌、漢陽兩岸分別同時向江中同時推進,全部鋼梁均由山海關、瀋陽橋梁廠製造,鋼材由鞍山鋼鐵提供;1957年5月4日,大橋鋼梁順利合攏,同日舉行了慶祝大會[29]。武漢長江大橋(連同配套工程)總投資預算1.72億元人民幣,實際只用了1.384億元;大橋本身造價預算7250萬元,實際只用了6581萬元[41]。
1956年6月,毛澤東從長沙到武漢,第一次游泳橫渡長江,當時武漢長江大橋已初見輪廓,毛澤東即興寫下《水調歌頭·游泳》一詞,其中廣為傳誦的一句「一橋飛架南北,天塹變通途」,正是描寫武漢長江大橋的氣勢和重要作用[42]。1957年9月6日,毛澤東第三次來到武漢長江大橋工地視察,並從漢陽橋頭步行到武昌橋頭[43]。
通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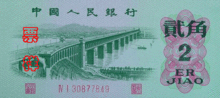

1957年9月25日,武漢長江大橋全部完工,並於當天下午舉行正式試通車;第二天的《長江日報》作了重頭報導,在《江花》文藝副刊上轉載了郭沫若不久前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一首《長江大橋》長詩。[44]
同年10月初,武漢長江大橋通過了國務院以王世泰為主任委員的大橋驗收交接委員會檢驗;10月14日,王世泰宣讀驗收結論,並代表驗收委員會批准大橋交付使用,由大橋局局長彭敏代表交方、鄭州鐵路局副局長耿振林代表接方在交接書上簽字。1957年10月15日,武漢長江大橋正式通車,並由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富春、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康生、陸定一、國家建委副主任王世泰、鐵道部部長滕代遠、交通部部長曾山、城市建設部部長萬里、蘇聯運輸工程部部長科熱夫尼科夫、蘇聯經濟總顧問阿爾希波夫等人主持了盛大的通車典禮。來賓講話完畢後,上午11時20分由李富春為鐵路橋剪彩後,由北京開往南寧、憑祥的19次旅客列車(今Z5次列車)成為第一列通過武漢長江大橋的旅客列車;隨後中央首長和中外來賓順序登上另一列列車通過大橋。中午12時,李富春又為公路橋上進行通車剪彩,三百多輛汽車組成的車隊、文藝花車隊伍順序通過公路橋面[32]。
正式通車當天晚上,李富春代表周恩來總理向參加大橋建設的蘇聯專家組組長西林授予感謝狀,滕代遠代表中國鐵道部向格洛佐夫等九位蘇聯專家(其中三位已回國)授予感謝狀和紀念章[注 1],又舉行了慶祝武漢長江大橋通車招待宴會。西林於1957年11月9日返蘇,並於回國後因管柱鑽孔法的成功獲頒列寧獎;他一生曾參與400多座大橋的設計建造,但武漢長江大橋一直是他最珍視的橋梁,曾多次表示武漢長江大橋不僅僅是一座大橋,更是中蘇友好的象徵;1980年10月,西林再次來華訪問,參觀了武漢長江大橋、南京長江大橋;1996年2月,西林於莫斯科逝世,家人按照西林的遺願在墓碑背面是刻畫了武漢長江大橋的形象,中國《人民日報》並發表了緬懷西林的紀念文章[45][46][47]。
|
武漢長江大橋正式通車的1957年10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用左側四分之一版面發表范榮康撰寫的社論《偉大的理想實現了》,旁邊是「李富春副總理參觀長江大橋」的圖片。10月16日,《人民日報》又以整個頭版報導長江大橋通車盛況,頭條標題是「火車飛馳過長江——千年理想成現實,萬眾歡騰慶通車」;並用幾乎通欄的版面刊登長江大橋的全景圖;還刊有「從北京開往憑祥的列車,在萬人歡呼聲中第一次馳過長江大橋」和「汽車隊伍浩浩蕩蕩通過長江大橋公路橋面」兩副圖片;一版同時刊登「表彰蘇聯專家對長江大橋的創造性貢獻,國務院授予西林同志感謝狀」的消息和西林的照片[48]。武漢長江大橋作為中國國內首座公鐵兩用特大橋,將京漢鐵路和粵漢鐵路兩路接軌,並於1957年11月11日合稱為京廣鐵路[49],成為京廣鐵路上最重要的「咽喉」。大橋建成後,列車過江時間由一個多小時縮短為幾分鐘,鐵路輪渡也失去了作用,於1958年停航。
武漢長江大橋將武漢三鎮連為一體,極大的促進了武漢的發展,不僅改變了民眾的出行和生活方式,而且為那個年代的武漢人民烙下了深刻的印記,成為武漢市最著名的城市標誌之一。大橋通車當年,許多武漢父母為剛剛出生的孩子取名時千方百計與「大橋」拉上關係,令取名為「大橋」、「建橋」、「漢橋」、「愛橋」等等的武漢人不計其數,據2007年的統計,武漢市戶籍人口中名字帶「橋」字的有28298人,其中八成以上是在1957年10月15日以後出生,共有22782人[50]。同時,武漢生產出的許多商品也以「大橋」作為商標,如大橋香菸、大橋味精、大橋童車、大橋縫紉機、大橋牙刷等。武漢長江大橋也是唯一一座曾分別出現在三套中國郵票上的橋梁。1957年10月1日,郵電部發行了《武漢長江大橋》紀念郵票(志號:紀43)一套2枚;1959年10月1日發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第三組)》紀念郵票(紀69)的第4枚、1976年7月16日發行的《到大江大海去鍛鍊》紀念郵票(J10)的第2枚主圖和背景也是這座大橋[51]。此外,武漢長江大橋的圖案也入選了1962年4月開始發行的第三套人民幣,作為反映當時「中國社會主義建設新成就」的一個重要標誌,成為第三套人民幣貳角券的主題素材[52]。
維護
武漢長江大橋設計通過能力每天為4.5萬輛汽車,由1950年代至1970年代,武漢的汽車擁有量沒有太大增長,日均汽車流量僅數千輛,大橋的運輸能力仍然能滿足需求。但從1980年代起,隨著汽車數量、鐵路運量大幅增加,至1980年代末大橋的日均汽車流量已經達到3萬輛、日均通過列車達170列,堵車的情況越趨嚴重。1995年,雙向六車道的武漢長江二橋建成使用,改變了「三鎮交通一線牽」的狀況,一定程度上緩和了武漢長江大橋的負荷。[53]雖然後來武漢又先後興建了白沙洲長江大橋、軍山長江大橋、武漢陽邏長江大橋,但武漢長江大橋的汽車流量仍然有增無減,至2000年代末,每天的汽車通行量已上升到十萬多輛、每天的列車通過量達到300多列;大橋上平均每分鐘有60多輛汽車通過,每6分鐘就有一列火車通過。
2002年8月至9月間,武漢長江大橋進行了首次大修,包括防滲、防鏽、路燈改造、路面重鋪等項目[54]。2007年,武漢長江大橋建成通車50周年之際,中科院專家測評,該橋的壽命至少在100年以上[55]。
由於武漢長江大橋是第一代長江大橋,其墩數較多、跨距較短,受船舶撞擊的機會率明顯較高,從1959年首次有記載的武漢長江大橋被船舶撞擊事故開始,大橋投入使用以來遭撞擊近百次。1990年7月28日,一艘重達900噸的吊船正面撞上,大橋養護人員為此維護了一個月。2011年6月6日清晨,武漢長江大橋遭遇建橋以來最嚴重的一次撞擊,因江面突起大霧,能見度極低,一艘萬噸級油輪撞上大橋7號橋墩,但對橋梁沒有太大影響[56]。
橋梁建築


建築結構
武漢長江大橋為鐵路、公路兩用橋,總長1670米,其中正橋1156米,北岸引橋303米,南岸引橋211米。上層為公路橋,車行道採用雙向四車道設計,寬18米,人行道每側各寬2.25米。下層為雙線鐵路橋,寬14.5米。正橋橋身為三聯連續橋梁,由3聯(3孔為一聯)9孔、跨度為128米的連續梁組成,共八墩九孔。碳素鋼桁梁採用菱形腹杆,H型載面。正橋的的兩端建有具有中國民族風格的橋頭堡,從底層大廳到頂亭有7層,內有電梯供人上下[57]。
美術設計
1954年1月,中央人民政府在關於修建武漢長江大橋的決定中特別指出,武漢長江大橋之美術設計,要配合大橋本身雄偉建築及武漢都市建築,並責成鐵道部設置獎金,廣泛徵求國內美術建築專家的優秀作品,送呈中央核定。至同年年末,鐵道部已經徵集到全國20多家設計單位和蘇聯專家的設計方案共25套[58]。1955年2月,包括茅以升在內,中國著名的建築、美術、園藝、都市計畫、橋梁專家們組成評委會,將25個方案分為一、二、三等獎,其中唐寰澄的方案為三等獎。評獎後,所有方案圖樣全部呈送政務院審批,周恩來當即拍板選定唐寰澄的第25號方案[59]。
唐寰澄曾參與武漢、南京、重慶、枝城、九江等長江大橋設計,而武漢長江大橋則是他的第一個設計作品。正橋橋身為外露的鋼桁梁結構,滿足了實用、經濟、美觀的美學原理,沒有增加過多的和結構無關的美術裝飾;而引橋上層採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連續拱形式,造成引橋和正橋在形式和材質上形成鮮明的對比。鋼筋混凝土結構的重檐四坡攢尖頂橋頭堡,自地面至公路面高為35米,造型為傳說中的「瓊樓玉宇」,橋頭堡的細節處理上又借鑑了中國傳統建築的形式,比如花格窗。大橋兩側有雕花欄杆,雕刻多取材於中國民間傳說和神話故事,如「孔雀開屏」、「鯉魚戲蓮」、「喜鵲鬧梅」、「松鼠吃葡萄」等[58]。在1985年黃鶴樓重建完工之前,武漢長江大橋的橋頭堡是武昌一帶的最高建築[60]。
對武漢人的城市記憶

自1950年代興建而來,這裡成為了武漢人的城市記憶,號稱每個武漢人都有跟它的合照。2017年長江日報徵集1957-2017年市民與武漢長江大橋的合影,60年間每年選一張登出,成為了珍貴的歷史照片記錄。[61]
參看
參考書目
- 鐵道部新建鐵路工程總局武漢大橋工程局. 《武汉长江大桥工程建设》. 1957.
注釋
- ^ 九位蘇聯專家包括阿·波·格列佐夫、維·依·卡爾賓斯基、恩·莫·戈洛托夫、阿·得·普羅赫洛夫、尼·依·波良克夫、尼·尼·吉洪諾夫、比·保·塔瑪洛夫、吉·格·柯斯金、米·謝·魯登科,因大橋建造過程中對鋼梁拼裝、機具製造、施工管理、培養幹部等方面,各有特出的貢獻,由中國鐵道部分別授予感謝狀。
參考文獻
- ^ 武汉长江大桥. 新華網. [2011-02-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2-14).
- ^ 武漢改革志編纂委員會. 武汉改革志. 武漢出版社. 2001: 32. ISBN 978-7-5430-2334-5.
- ^ 3.0 3.1 3.2 凌鴻勛. 《中国铁路志》. 台北: 世界書局. 1963年: 416-420.
- ^ 蔣太旭、陳麗芳. 张之洞:最早提出建设武汉长江大桥. 《長江日報》. 2011-03-20.
- ^ 經盛鴻; 南京大學. 中囯思想家硏究中心. 詹天佑评传.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245.
- ^ 中国科技史料, Volume 17.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1996: 34–35.
- ^ 劉振傑. 汉阳史话. 武漢出版社. 2004: 32. ISBN 978-7-5430-2911-8.
- ^ 中國鐵路橋梁史編輯委員會. 中国铁路桥梁史. 中國鐵道出版社. 1987: 129.
- ^ 經盛鴻; 南京大學. 中囯思想家硏究中心. 詹天佑评传. 南京大學出版社. 2001: 254.
- ^ 孙中山研究论集 纪念辛亥革命九十周年.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2001: 21.
- ^ 11.0 11.1 吳之凌、汪勰. 武汉城市规划思想的百年演变. 《城市規劃學刊》 (上海: 同濟大學). 2009年4月, 182. ISSN 1000-3363.
- ^ 凌鴻勛. 中國鐵路槪論. 國立編譯館. 1950: 62.
- ^ 长江第一桥-----武汉长江大桥蕴藏的故事_若愚_新浪博客. blog.sina.com.cn. [2018-03-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5).
- ^ 皮明庥. 武汉通史 (民国卷下). 武漢出版社. 2006: 6. ISBN 978-7-5430-3296-5.
- ^ 15.0 15.1 1949—1990年重大工程项目建设规划. 武漢市志辦. 2007-07-03 [2011-08-27].
- ^ Team, Discuz! Team and Comsenz UI. 民国时火车是这样过长江的|记武汉长江大桥的前世今生. www.deyi.com. [2018-03-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5).
- ^ 蔡雙全. 湖北抗日战争史, 1931-1945年. 武漢大學出版社. 2006. ISBN 978-7-307-04751-8.
- ^ 中国铁路运输. 中國鐵道出版社. 1994: 11.
- ^ 京广铁路百年沧桑. 西南交通大學鐵路發展有限公司.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9-05-02).
- ^ 武汉解放史料:大事记(1946年). 武漢市地情文獻.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6).
- ^ 武汉长江大桥_用脚步丈量地球儿_新浪博客. blog.sina.com.cn. [2018-03-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5).
- ^ 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略 工程技术编. 交通卷. 中國鐵道出版社. 1995: 202.
- ^ 我国桥梁界先驱李文骥. 廣州文史.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5).
- ^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 2011-09-21 [2016-11-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2-28).
- ^ 湖北省志: 城乡建设 (下). 湖北人民出版社. : 549.
- ^ 武汉文史资料选辑, Volumes 55-58.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94: 80–83.
- ^ "中國鐵路建設史" 編委會. 中国铁路建设史. 中國鐵道出版社. 2003: 363. ISBN 978-7-113-04911-9.
- ^ 當代中國叢書編輯部. 当代中国的铁道事业 (上).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1990: 481.
- ^ 29.0 29.1 29.2 29.3 1957年:武汉长江大桥建成通车. 武漢黨史網.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1-06-14).
- ^ 武汉市志: 交通邮电志, Volume 12. 武漢大學出版社. 1998: 253–254.
- ^ 湖北省志: 城乡建设. 湖北人民出版社. : 77.
- ^ 32.0 32.1 32.2 滕久昕. 父亲滕代远参与领导武汉长江大桥修建始末. 《世紀行》 (武漢: 湖北省政協辦公廳). 2010年9月: 5–12. ISSN 1005-0647.
- ^ 缅怀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康·谢·西林. 中國人民對外友好協會. [2011-08-27].
- ^ 茅以升. 武漢長江大橋. 科學普及出版社. 1958: 33–34.
- ^ 武汉文史资料, Volumes 36-37.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北省武漢市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1989: 105.
- ^ 共和国成就大辞典. 紅旗出版社. 1993: 220.
- ^ 武汉市交通邮电志:铁路枢纽. 武漢地方志編纂委員會辦公室.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3-10-29).
- ^ 中國鐵路橋梁史編輯委員會. 中国铁路桥梁史. 中國鐵道出版社. 1987: 146.
- ^ 万里长江第一桥,通车60载、传奇两百年! 超级建筑文章. www.yxtvg.com. [2018-03-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8-03-25).
- ^ 武汉长江大桥桥墩基础工程基本完成. 新華社. 1956-10-25 [2011-09-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1-07).
- ^ 遭受万吨油轮等70多次撞击仍健康. 杭州日報. 2012-10-16 [2016-11-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4-28).
- ^ 中囯百年历史名碑. 遼寧敎育出版社. 1999: 519.
- ^ 中國交通運輸協會. 中国交通年鉴. 中國交通年鑑社. 1994: 5.
- ^ 武汉长江大桥历史背景. 武漢文明網. [2018-03-2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5).
- ^ 武汉长江大桥创新采用管柱钻孔基础. 荊楚網. 2007-10-15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 ^ 长江大桥通车50年 风雨半世纪. 武漢交通政務網.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10-11).
- ^ “武汉长江大桥是最好的!”. 2007-10-12 [2011-08-27].
- ^ 袁晞. 《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从范荣康先生的讲述中回首往事》.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ISBN 9787010078618.
- ^ 世界最长高速铁路 为“中国梦”提速. 經濟日報. 2012-12-26 [2018-09-24].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4-05).
- ^ 武汉631名市民与大桥同庆50岁. 楚天金報. 2007-10-15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7-17).
- ^ 邮票上的长江大桥. 安徽日報. 2004-12-17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07-12-25).
- ^ 中国制造之科技第四期 武汉长江大桥. 網易. [2016-11-02].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8-25).
- ^ 武汉拟投1.7亿元大修长江二桥. 荊楚網. 2012-02-03 [2017-12-13].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4-05).
- ^ 武汉长江大桥进行首次大修. 新華網. [2011-09-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03-04).
- ^ 武汉长江大桥寿命可逾百年. 荊楚網. [2011-02-19].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2-07-17).
- ^ 万吨船队撞击武汉长江大桥桥墩 撞击声如同雷鸣. 2011-06-08 [2011-08-2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7-11-12).
- ^ 中国文化之最. 中國旅遊出版社. 1991: 999.
- ^ 58.0 58.1 許遠、黃李濤. 武汉长江大桥解读. 《華中建築》 (武漢: 中南建築設計院). 2010年11月, 28 (11): 166–169. ISSN 1003-739X.
- ^ 人民鐵道出版社, 北京. 修建中的武漢長江大橋. 人民鐵道出版社. 1956: 25.
- ^ 在长江上修大桥毛泽东对武汉情有独钟. 中國橋梁網. 2010-08-31 [2016-11-07]. (原始內容存檔於2016-11-07).
- ^ [早安武汉]每个武汉人都有跟TA的合影,今天祝它生日快乐!. 長江日報. 2017-10-15 [2020-07-08].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08).
外部連結
- 歷史照片合集:長江日報徵集1957-2017年60年間市民與武漢長江大橋的合影,每一年選一張登出的合集: [早安武汉]每个武汉人都有跟TA的合影,今天祝它生日快乐!. 長江日報. 2017-10-15. (原始內容存檔於2020-07-08).



